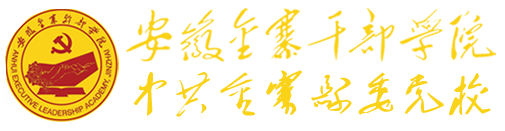





4月27日 星期五 晴
新疆十点上班,人们习惯十点半以后上街活动。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没有见到所要走访的老红军近亲属,只好参观西路军“新兵营”。“新兵营”,即西路军失败后,由李先念等人率领突围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的400多人所组成的西路军总支队,对外称“新兵营”。在展板上,我们仔细寻找熟悉的金寨籍老红军的名字,每找到一位都兴奋一下,为他们劫后余生而感到欣喜。我找到新兵营讲解员和负责人,想从他们那里找一些有关的书籍和文字材料。得到的答复是“没有专门的书籍,文字材料需要宣传部门审批才能外传。”无数指战员血洒西征路,能幸存的很少。特别是从金寨走出去的许多幸存老红军,现在,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找不到,更难知道他们生死征战的点点滴滴故事,不由得心里很酸楚、灰心。
从“新兵营”出来,我们去哪里?一位来自山东的新兵营老保安说:想了解西路军历史可以去哈密西路军纪念馆或乌鲁木齐八路军新疆办事处,那里可能有你们想要的东西。我们驱车,左拐右转(不熟悉乌市交通),在一个下坡路口看到五星红旗和一栋插着彩旗的小红楼,感觉可能是“八办”,停车往回走100米左右,到了“八办”的大门口。结果大门关闭,门前有一方告示牌,“八办”维修持续到9月30日,我们只好沮丧地离开。
在乌鲁木齐市双拥办的郭处长引领下,我们去了乌鲁木齐烈士纪念馆。路上,他给纪念馆打了一个电话,车进入纪念馆时,纪念馆的书记、馆长等人已在等候。寒暄之后,书记了解了我们的来意。就带着我们参观纪念馆各展厅。纪念馆主题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馆内有七个厅,前三个厅都有西路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挥师进疆的内容。在这里,我们看到更多的金寨籍老红军以及他们参加的大大小小战斗的故事。有些资料,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我对资料和图片很感兴趣,想要一些。由于权限的原因,纪念馆无法满足我们的要求,赠送了一套纪念馆的宣传图集。
在书记的带领下,我们瞻仰了乌鲁木齐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是为纪念新疆解放而新建的纪念碑。纪念广场干净整洁,纪念碑气势宏伟,烈士陵园庄重肃穆,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沿着拾级而上,纪念碑后面有两排烈士陵墓,每排都有五位烈士,墓碑非常醒目。我们缓步瞻仰,默读碑文。第二排第一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一代飞行员汪德祥,他是从金寨走出去的老红军。1916年,汪德祥出生于金寨县槐树湾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丧父,母子相依为命,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1929年,金寨境内爆发了商南起义和六霍起义,在那充满激情的岁月里,汪德祥报名参加了红军。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汪德祥随部队西去川陕,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三过雪山草地,汪德祥饱受磨难。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宁会师后,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经宁夏、内蒙古、新疆到苏联“国际路线”的任务。此时,汪德祥任红四方面军总部机要科译电员。由于种种原因,西路军惨败,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汪德祥等400多人突出重围,打到迪化城西的阜新纱厂。在这里,汪德祥经历了军旅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打着抗日救国旗号,扩建新疆督办公署边防航空队,设立航空训练班。中共中央与盛世才多次谈判达成协议,为中共培训60名航空人员,由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邓发具体负责选调学员。1938年3月,选调的43名学员分成两个班,飞行班25人,机械班18人。飞行班中有4名金寨籍学员,分别是方华、方子翼、王东汉和汪德祥。当时,汪德祥他们文化程度很低,学习飞行技术成为一个不小的拦路虎。可是,这些打仗不怕死、遇事不服输的红军学员,发扬红四方面军“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以勤补拙、互相帮助、刻苦学习、认真操练,胜利完成了30多门航空理论科目学习。无论是理论学习还是飞行实习,汪德祥的成绩都是遥遥领先。十分不幸的是,1942年6月9日清晨,汪德祥兴致勃勃地同战友们来到距迪化90公里的临时野外飞机场上,他满怀豪情地驾驶一架双翼战斗机升向3000米高空,开始了高难度技术飞行训练。平时,他对飞行技术精益求精,严格要求自己,从不马虎。这天,当他做完大小坡度的盘旋急转弯之后,开始翻滚表演,第一次做得不够理想,于是又进行了第二次特技训练。突然发生意外,飞机旋转速度出现了异常,刹那间飞机由翻滚变成了螺旋下降。为了保住飞机,汪德祥放弃了跳伞逃生的机会,结果坠地牺牲,年仅26岁。事先,我们不知道汪德祥烈士的陵墓在这个陵园,没有准备花篮或鲜花。走出烈士陵园,一路上,心生愧疚,总感到对不起先烈,没有表达缅怀之情。
时间已过12点,我们准备告别纪念馆领导,可是书记一定要留我们吃中餐。盛情难却,我们提出吃个简餐吧,书记同意了。就在纪念馆旁边的农家乐,我们每人吃了一碗干拌面。在返回旅馆途中,纪念馆电话求证我们的单位名称和人员姓名,准备在内部网站发布我们活动的信息。我的同事说,纪念馆对我们的工作很重视、很细致,宣传工作做得也及时。
下午,在我们再三邀请下,我们选择一家肯德基店,采访金寨籍老红军胡孝炳的孙女。她是在忙完旅游公司的繁重工作之后,抽空来见面的。我们给她买了一杯咖啡、一份鸡翅,匆匆忙忙地采访了她。可是,她对爷爷的人生经历知之甚少。
问:新兵营展板上,几处写着你爷爷的名字,你知道吗?她只是笑笑。
追问:你们搞旅游,不带团队去新兵营吗?她淡淡地说:我主要搞行政工作,没有带过团队,而且新兵营一般游客不去那儿。
问:你对爷爷有什么印象?她断断续续地说:爷爷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卫生队的医生,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生活简朴,印象中,爷爷总是穿着警服或者旧的中山装。爷爷不计较个人经济待遇,作为师级干部,好像一直是17级。
问:你知道爷爷当红军时的故事吗?她喃喃地说:爷爷生前不怎么说这些……偶尔,他的战友张爷爷来,他们谈论战争年代的事情,我听不懂。
追问:爷爷去过北京吗?他有没有写过回忆性文章或留下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她肯定地说:没有。爷爷生前使用的物品都很破旧,爷爷去世后,我们搬家了,那些物品绝大多数都没了。有些照片,都在我母亲那儿,具体是些什么照片,我没有印象了。
最后,我们请她帮忙,能否联系她的母亲或舅爷,了解一些关于胡孝炳老红军的事迹。例如,据说洪学智上将曾赠送给胡孝炳老红军一块PLAYBOY牌手表,我们想求证真实性和其中故事,她答应试试看。可能因为职业的局限性,我有一丝责备的情绪:如果我的爷爷是一位老红军老革命,我能不能说出他的几个完整的小故事呢。
回到宾馆,我们等待另一名老红军李连贵的小儿子李继东夫妇。十八点,当我走进同事的房间时,采访已经开始了。
李连贵,金寨开顺人。1931年5月,带着外甥储士明参加了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时期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新四军的战斗生活。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公安局提篮桥监狱一支队支队长。1952年,押解提篮桥等监狱重刑犯3000人,转场延安(任西北延安劳改大队大队长)到新疆。正值新疆用人之际,留在新疆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工程支队长、后勤部政治委员。1975年4月,生产建设兵团体制撤销,农六师随之撤销。198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决定》,随后,农六师建制恢复,李连贵曾任农六师政委。
在新疆,李连贵参与组织了新疆猛进水库、八一水库、马桥水库等大型水利设施建设,为军垦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深受干部战士和军垦群众的信任和拥护。1969年国庆节,新疆有60位代表赴京参加国庆活动。其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9人。毛主席邀请新疆13位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并接见了他们,李连贵就是其中一员。
李连贵经常对子女说:虽然我官不大,但能看到新中国成立,而且还弄了一大家子人,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很满足了。现在国家很困难,我们不能要求太多。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李连贵每月工资不到200元。这么一点钱,他时常拿出钱帮助金寨的三个哥哥、江苏的二个兄弟和新疆的众多战友,每个月都要寄出几十元钱,我们看到几张李连贵夹在一个小本子里的60.70年代寄钱的邮局凭证。有一天,李连贵上街买菜,路过长途汽车站,发现自己从上海带来的一个战士,就问:你怎么在这里?那个战士说:家里人生病来乌鲁木齐治病,没有钱,住不起宾馆,自己就住在车站里。李连贵把他领回家,给他做饭吃,临别时,送给他50元钱。李连贵去世,那位战士得到消息后,骑自行车赶了几十公里前去悼念,说起李连贵救助他的那件事,还是感动不已。李连贵从上海带到新疆的一个团人,全部留在阿克苏106团,只有他一个人被调到农六师。所以,阿克苏过来的人,都把李连贵的家当作一个大饭店和公共旅馆,吃住都在他家。从1952年到1979年的27年里,李连贵没有加过工资。这期间他有五、六次加工资的机会,全部让出去了,让低工资的职工涨工资。直到1979年离休时,按照级别待遇,他的工资才涨到600多元,增加了不少。李连贵从上海大都市,无条件到新疆,留下来,带领干部战士建水库,修水利,生活得很艰苦,但他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人的乐观向上、一心为民的初心。今天,我们有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忘记了“群众利益无小事”,先人后己,加薪政策还没有出台,就盘算着自己怎么加,或者今年评优要、明年评优还要,希望名利兼收,三年上一个台阶。
跟随李连贵到新疆并转业到兵团的郭慧琴曾对李继东说:继东呀,你爸爸那个时候总是跟我们开玩笑,说“你们好好干,我今天给你们炖红烧肉吃。”可是,到吃饭时,哪有红烧肉呀,能吃饱饭就不错了。有时,你爸爸想方设法弄点肉,每人碗头上有那么一片肉。但我们听他说吃肉,心里可有劲了。
为了解决新疆缺水问题,李连贵参加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系列水利建设工程。新疆地域辽阔,地形地貌特殊,作为一线建设指挥者,李连贵很少用车,全程骑马。所以,有一件东西从延安到新疆一直带在身边,那就是马鞭子。新疆的冬天零下30多度,有时从工地回到师部开会,李连贵都是晚上骑马,最远处到师部80多公里,一路策马奔驰,赶到师部,帽子、身上挂满冰霜。李继东说:后来,组织上给爸爸配备一辆苏式吉普车,骑马少了,可是马鞭子还随手用。那年,李继东八、九岁,与小车司机很要好,偶尔,背着爸爸蹭车。李连贵知道后,就用那个马鞭教训过李继东,并说以后再蹭车,我就用它抽死你。家里还留下一幅旧马掌,看到马掌,就想起爸爸他们那代人,常年风尘仆仆,深入基层,很多时间是在马背上办公、充饥。小时候,自己对爸爸很陌生,七、八岁之前都是管爸爸叫叔叔,为什么呢?不认识。有时还纳闷,这个人怎么有时住在我们家?他们那代人,革命理想大于天,抛家别子,忘我工作。今天,铭记历史,传承基因,新疆维稳、脱贫攻坚都需要这种担当和奉献精神。
李连贵有一块手绢,那是在解放上海时,部队进城后买的。1952年,陈毅市长召开上海市公安局领导人工作会议,部署把提篮桥监狱等3000多名重刑犯押解到延安转场到新疆,这是一个风险很大的工作。当时,有的领导以父母年迈多病或者妻子待产或自己负伤身体不好为由不愿冒险。看到这里,李连贵自告奋勇,承担押解工作。陈毅市长说,人押到了,你们就回上海。到新疆后,王震说,新疆正缺干部,你们不要回去了,就在新疆工作吧。结果,一留下来就永远留在了边疆。为了革命献青春,为了新疆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李连贵儿媳说,那副手绢洗得都泄了,像渔网,舍不得丢。我们从很多影视作品中看到,解放军进入大都市后,过去从农村出来一直行军打仗的干部战士,他们开始接受现代文明生活习惯,例如,不随地吐痰。李连贵把这块手绢带到新疆,也是把现代文明生活习惯带到了新疆。
这些小故事说明,共产党人不仅有打天下的能力,更有治天下的优良作风和治天下的精神境界。无数李连贵锻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文明之师、威武之师、人民子弟兵。农六师师部所在地五家渠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仅是一个五户人家依一条土渠而居的无名小村。中华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第六军第十七师一路西进,进驻新疆乌鲁木齐、伊犁等地区,扫除战乱,建立人民政权,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时任十七师师长的程悦长(湖北红安人,开国少将),率部进军阿勒泰剿匪平叛途经五家渠,看到这片土地一马平川、草丰水足,难掩兴奋之情,说:“有朝一日在这里建一座最漂亮的城市,名字就叫五家渠市……”1951年秋天,程悦长为修建水库做着筹划准备工作,以十七师(农六师前身)战争年代的代号命名为“猛进”水库。那时,新疆刚解放,粮食奇缺,部队吃的大都是从苏联进口的列巴,还要加些野菜。六军军长罗元发(福建龙岩人,开国中将)深知程悦长在战争中曾经多次负伤,身体虚弱,对送给养的参谋长冯配岳说:“这50斤大米,是专给程悦长师长的,他身体不好,又是南方人,让他吃点稀饭。”给养运到了奇台,冯配岳向程悦长报告说:“部队给养运到了,还是列巴,有点大米是军首长专门分配给你的”程悦长高兴地问:“大米有多少?”冯参谋长答道:“只有50斤。”“50斤也是军首长的一片心意,我很感激,但还是分给大家。”冯参谋长坚持说:“大米不能分,是军首长给你的。”稍停了停,程悦长突然向冯参谋长提出一个与大米不相干的问题。师长问:“参谋长,咱们部队进疆,路经酒泉,酒泉因何而得名,你讲给我们听听吧。”参谋长一时弄不清楚他的意思,师长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又不能不回答,于是就说:“我也是听来的,不知对不对。据说汉朝有个大将名叫霍去病,因出征有功,汉武帝就给他赐了御酒一坛,以表彰他的功绩。但酒少人多,分饮不过来,霍大将就把酒倒在泉内,与众士兵取泉水共饮,酒泉因此而得名。”师长笑着说:“你讲得好,一个封建王朝的将领,尚且能与士兵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难道共产党部队里的一个师长,就不能与战士一起吃列巴,而要吃大米饭吗?”师长终于说服了参谋长,将50斤大米平均分给了各个单位。程悦长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伤痕累累,流血流汗,操劳过度,艰苦的岁月耗尽了他的精力,最终身染疾病,不得不离开新疆到北京治疗。养病期间,他在病床上给农六师政委赵予征(山西沁县人,1972年任农七师政委,1980年6月任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写信。在信中嘱托:“我们这些干部,上边一个命令,说走就调走了。可是跟随我们的那些老战士,他们是调不走的,要在边疆扎根,建设新疆一辈子,一定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帮他们建家立业,解决好他们的婚姻问题,对他们负责到底。”李连贵的婚姻就是组织关心的结果。妻子王长英,江苏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征兵入伍,曾在提篮桥监狱担任看守工作,看管过大汉奸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组织介绍下,与老红军李连贵结为夫妻。李连贵四十岁时,有了第一个孩子,一生养育了四女二男。王长英跟随李连贵吃了不少苦,在新疆聚少离多,操持着娘婆二家以及李连贵战友的生计。上个世纪60年代,响应国家精简机关人员的号召,作为领导干部,李连贵首先把自己的妻子减掉了,从此王长英变成了一个家庭主妇。她们的六个孩子都参加了上山下乡,都被分配到最艰苦的农村。小儿子李继东说:下乡当初,整田插秧,几天下来,双腿红肿。回家对爸爸说:“这个活太重了,自己实在做不了,希望爸爸关照一下。”李连贵训斥道:别人家的孩子能干,你也应该能干,没有同意。小女儿李晓琳是同期上山下乡最后一个回城的知青。回城后,招工进入拖拉机厂。80年代末,拖拉机厂下岗分流,李晓琳第一个被解除劳动合同。下岗后,李晓琳做过临时工、帮人看过商店、当过服务员,打零工过活,遭人白眼。许多同学不理解地说:你爸爸是农六师政委,管着农六师的工、农、商、学、兵,权力不小,怎么就不能为子女谋一份工作。